文:梅莉莎・達爾(Melissa Dahl)
在我跟阿爾斯托聊上天的許久之前,我就知道了他故事的結尾。我開始在網路上搜尋他的事蹟,而且用的是一種我通常保留給過去曾經對我不好過的人,那種我想看到他們現在慘兮兮的那種熱情。結果我查到他從庫班那兒談到了令人稱羨的合約,由庫班出資十五萬美金換得塔爾槳板公司三成的股權,外加阿爾斯托未來投資新事業時的優先認股權。自從他僵在台上的那一集播出後,塔爾公司賺進了超過兩千五百萬美元的營收,而庫班也說這是他在節目上做過最棒的投資。我在《豪爾.史登秀》(Howard Stern Show)上找到庫班在當中提到了阿爾斯托的訪談,但庫班在過程中是「報喜不報憂」,只誇阿爾斯托的成就,而隻字未提他簡報時有多糗。「他經營企業眼光獨到,」庫班這麼對主持人史登說,「公司成長之快,讓我又多掏出了些錢來對他投資。」
聽著,我很希望這個故事的啟示是把尷尬的瞬間給忍下來,我們就可以百發百中地名利雙收,但要尷尬真的可以換錢,那我早就該發了不是嗎?事實上,阿爾斯托的故事是「聚光燈效應」(spotlight efect)一種一翻兩瞪眼的電視版本。
你有沒有過一種經驗是在讀到一段文字後,自己的人生觀與生活方式都有所改變了呢?我希望有,而且我希望這段文字是出自某本小說,或者是古代哲學的經典,又或者是聖經等宗教典籍的故事。小說、哲學經典與宗教典籍,都曾經讓我從中得到深刻的體悟,但幾年前讓我心有所感的,卻是一本讓人感覺有點「書呆子」的出版品:二○○○年的某期《性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》(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)上登了一篇文章。對於自我意識很強的人來講,這是一篇讓人如沐春風的文章。二○一五年,耶魯心理學者保羅.布魯姆(Paul Bloom)在為《亞特蘭大》雜誌撰文介紹這項研究時,也有跟我一樣的看法,他也認為這研究所導出的觀念可以改變人生。布魯姆教授是對的。
作為那一篇論文核心的實驗,其實並不複雜,而且內容說來還相當有趣。諸位學者——在康乃爾大學湯瑪斯.吉洛維奇(Tomas Gilovich)教授的率領下——以尷尬為題,設計了一些可憐的志願者。學者們首先是故意提供了錯誤的實驗報到時間,好讓被設計者比其他人都遲到五分鐘。等他或她們姍姍來遲,學者又會堅持要這些可憐蟲換上爆笑的超大T恤,上頭印著美國老牌歌手貝瑞.曼尼洛(Barry Manilow)的大照片(話說曼尼洛是心理學界研究尷尬主題時很愛用的元素。除了拿印著他大頭的衣服叫人穿上以外,還有研究者會要受試者唱他的拉丁名曲——科帕卡巴納夜總會!〔Copacabana!〕——給槁木死灰、面無表情的觀眾聽)。
在穿上T恤後,這些被陷害遲到的受試者會被送進一間教室裡,而在那兒等著他們的是其他已經集合完畢的受試者——但他或她會還來不及坐下,就被告知說經過評估,老師們覺得其他受試者的進度都超前太多了,所以他們希望這些身穿曼尼洛T恤的志願者能離開教室,另行參加一對一的實驗。
你可以想像人在這個狀況下,會有多麼困惑。但他們還是乖乖地轉了身,離開了教室,然後在走廊上遇到了另一名研究人員。這名研究人員會開始問他們一堆問題,表面上是要測試受試者的短期記憶,但學者們感興趣的其實只有一個問題:他們覺得教室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們身上的爆笑T恤,而且還能講出被網版印刷在上頭的歌手大名?
大概一半的人會記得吧,多數被設計的學生說。但事實上,教室裡會記得那件曼尼洛T恤的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而已。換句話說受試者的推測,遠比實情來得高出很多。確實,有人會記得那件爆笑的T恤,但人數也確實沒有受測者想像中的那麼多。這種認知偏誤,被吉洛維奇與同僚稱為「聚光燈效應」:我們會高估別人對我們一舉一動或外表的重視程度。對於自我意識很強烈的人而言,這個結論堪稱喜事一樁。畢竟選擇貝瑞.曼尼洛元素的用意,就是要讓人覺得受試者的穿著很惹眼,很莫名其妙——我還是個少女的超酷表妹在不認得貝瑞.曼尼諾是誰之餘,也肯定會覺得這T恤尷尬到不行。但要是連故意讓人尷尬的事物,都壓根不像我們以為的會有那麼多人注意的話,那不小心弄來的尷尬,我們又何苦在心上耿耿於懷呢?
放自己一馬吧。你襯衫上的咖啡漬,就算了吧。你第一次約會時說的奇怪發言,或是用投影片簡報時發生的大暴走,也就讓它過去就過去了吧。沒那麼多人閒著沒事幹,會一直盯著你的錯誤看。
關於曼尼洛研究還有一點值得玩味:即便沒有那件刻意搞笑的T恤,實驗結果也不會受到影響。在同實驗的另外一個版本裡,學者讓遲到者穿上的事傳奇雷鬼樂手巴布.馬利(Bob Marley)的T恤,這在事前針對一組大學生評判的投票中,是屬於放在T恤上不會太糟糕的圖案。而同樣在這次的實驗裡,受試者還是嚴重高估了旁人注意他們穿著的程度。不要不相信。這就像很多人曾經滿心期待地帶著新髮型去上班,癡心妄想著會在辦公室引發轟動,結果同事上司根本都無動於衷。如何,還蠻準的吧。有句話不是常聽得人說:「別太擔心別人怎麼看你,別人根本很少會看你。」
但有的時候,吉洛維奇告訴我,分享這項研究似乎會引發應外一種極端的效果:這個研究的發現會被過度簡化為一種膚淺的社交虛無主義——怎麼樣都無所謂了!我們想怎樣就怎樣吧!反正也沒有人會看,不是嗎?又或者就當身邊沒人在看,盡情跳舞吧,反正真的沒人會看啊!但這麼去解讀「聚光燈效應」,總還是讓我內心有一點點甩不開的疑慮。這種解讀,跟我覺得自己對身邊眼光非常在意的事實,要怎麼樣才能彼此相容而不衝突呢?
就前幾天的事情,我走在一對十來歲的情侶身後。男生抓著女生的手臂——更精確地說是他抓著女生的手肘。男生手放的位置,讓女生的前臂彎成了看起來很不舒服的負四十五度。他們就這樣走了一條整街,然後以這麼輕的年紀來說很難得的貼心,女生溫柔地伸直了手臂,而男生也收到了訊息:他放開了女伴的手肘,改成跟她手牽著手。這對小情人在下一條街左轉,而我則繼續直行,目標是溫暖的家裡。
從頭到尾,他們都沒發現有個背後靈在一邊觀察他們,一邊回憶自己曾經尷尬無比的青春與愛情(我們在他家的沙發上看《門當父不對》(Meet the Parents)的DVD,看著看著他靠了過來,想把手臂繞在我的身上,但角度沒算好,所以他手肘卡住了我的大頭)。
有些比較新的研究在二○一七年初問世,由此聚光燈效應的現象與內涵,又有了更多的層次可以分析。不想被吉洛維奇團隊給比下去的這一群研究者——在艾瑞卡.J.布斯比(Erica J. Boothby)這名耶魯心理學研究生的帶領下——給他們有興趣進行「切片」研究的社會互動取了個也很帶勁的名字:「隱形斗篷幻覺」。透過這個名字,他們想指涉的是多數人出門在外,都免不了會有的一種矛盾觀念,那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自己可以卯起來觀察別人,但別人都不會在看他們。
這是一種「螳螂捕蟬,但覺得黃雀不會在後」的概念。「因為這種幻覺的存在,所以你會不論在飛機上,還是在餐廳裡,甚至在牛仔競技大會上,都會沒注意到一件事情,那就是你可以把眼光從別人身上移開⋯⋯開始忙起任何一件別的事情——別人當然也可以停下手邊的任何一件事情,專心來觀察你。」布斯比跟她的同僚如此寫道。
我常很認真觀察人,但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別人日常的觀察對象。要是我可以在通勤的途中觀察人生百態,那別人怎麼就不能在交通工具上觀察我的一舉一動呢?何以我有時候會自認為是飄泊在人生中一朵沒沒無聞的浮萍,有時候又覺得自己萬眾矚目,無所遁形呢?換句話說,我要如何在聚光燈效應與隱形斗篷幻覺之間,扮演好和事佬呢?
這麼些問題,每一個都是布斯比偕同事想透過一系列實驗來解開的謎團,而這些實驗的結果,則被發表在《性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》。在其中一次實驗研究,他們請志願者——兩兩一組向社會心裡學實驗室報到。但等約好的時間到了,志願者卻在報到處被告知自己遲到了,然後重新等待的時間他們可以自行利用,不管是要看報,玩手機,或是發呆放空都行——沒有人會干預。就這樣五分鐘過去了,一名看起來滿懷歉意的研究人員現身,並將來報到的人帶進個別的房間來進行實驗。
惟事實上,等候室所發生的事情,才是真正的實驗內容。在被帶進去的個別房間裡,每個人會被發給一份問卷,上頭問的是他們對在等候期間的另外一人記得多少。另外,他們還會被問到自己觀察對方的用心程度是高是低——他們認為對方觀察自己的用心程度又是高是低。「雖然每個人都像情報員一樣注意著彼此的各種細節——衣服搭配、個性、心情——但我們發現受試者會有志一同地認為對方沒怎麼在看自己,甚至完全沒在看。」布斯比在《紐約時報》的論壇撰文中這麼談到自己的研究。
有的時候,你會覺得自己是矚目的焦點,但有的時候,你又會覺得我自個兒忙自個兒的,應該沒有人會把我當回事兒吧。問題出在你假設你深陷其中在注意的事情,也是別人注意的事情,但這一點往往與事實不符。
要把聚光燈效應與隱形斗篷幻覺兜攏在一起,我們可以引用心理學者所說的「定錨與調整」。為了把此心與人心之間的鴻溝橋接起來,合理的做法是我們要先了解自己腦袋瓜裡在想些什麼,這就是所謂的「定錨」。定錨完成之後,再來就是「調整」:你可以試著調整你的視角,想想世界在別人的眼中是什麼模樣。問題是,按照心理學研究與我過去的經驗一再顯示,在於我們調整的幅度往往不夠。
這樣的事情,曾經在實驗室裡證實過;在其博士論文中,如今在威廉斯學院(Williams College)任教的心理學者肯尼斯.薩維茨基(Kenneth Savitsky)讓他的研究對象準備並發表演講,而上台演講怎麼講,都一定是會讓人有點緊張的事情。不少受試者都顯得緊張兮兮,而他們也都認為台下的聽眾會感受到他們的焦慮情緒。但事實是聽眾並沒有那麼敏銳,至少沒有發表演講者所認為的那麼敏銳。
在另外一個相關(而且甚妙)的獨立實驗中,研究者請學生逐一進入實驗室,然後讓他們在一張擺了十五個同型杯子的桌邊坐定。每個杯子都裝紅色的神祕液體:其中十個杯子裡是櫻桃色的Kool-Aid(廉價果汁),另外五杯則是由「水、紅色食用色素、包裝醃葡萄葉用的醋液滷水」混合而成,讓人十分費解的汁液。嗯嗯。受測的同學們得到的指示,是要每杯都淺嚐一下。研究者向他們保證雖然每一杯喝起來會有微妙的差別,但對身體絕對無害。實驗的過程全數錄影存證,而在品嘗過紅色液體後,學生們被告知有另外一組同學會在看過影片會推測誰喝的是滷水,誰喝的又是普通的人工果汁,而很顯然飲用者的臉部表情會是唯一的線索。由此負責喝的學生會被交付另外一項任務,那就是猜測在每十名觀察者當中,有幾位能夠猜對杯中物為何,而平均起來,他們認為猜對的人會有五個左右。
結果顯示學生會很穩定地高估能猜對他們表情的人數,而對此學者所提出的假說,是認為學生無法區分出哪些是他們對自身的了解,哪些是別人能透過觀察而對他們取得的理解。「受試者知道自己喝的是好喝還是不好喝的飲料,但除此之外,他們恐怕也無從判斷觀察者能夠看出什麼名堂。」研究的作者們說。
心理學者給這種現象取了一個名字叫「透明度幻覺」(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)亦稱「獲洞悉幻覺」:只因為自己的感覺很強烈,我們就會認為別人可以從我們的臉上判斷出這一點。但大多數時候,這依舊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。你可以將之稱為「自知的詛咒」。
試想。你最熟悉的主題是啥?什麼東西你覺得跟自己的心神距離最近,甚至最親?答案是你自己。你研究自己已經一輩子了。你是全球研究你的第一把交椅。你對自己的了解極深,所以你難免會期待別人看你跟你自己看你是同樣的角度,而這正是「無法消弭的鴻溝」會如此令人震驚的一個原因。你要是會因為身穿印著貝瑞.曼尼洛大頭的巨大T恤而覺得手足無措,那你就很難走出那種感受而進入到房間裡其他人的心中。在做簡報的時候會緊張到手足無措,代表在你的想像裡,所有人都可以從臉上讀取到你的惶恐。你會以為別人可以接收到你的尷尬,你會以為這個瞬間對你而言非常突出,所以它對別人也一定一樣明顯。
我們來想想在其他領域裡,專業代表著什麼意義。「如果你是專業的物理學者,那通常代表你能注意到各式各樣別人注意不到的細節。如果你是專業的數學家,那代表你有本事看著方程式,然後注意到菜鳥會忽略掉的奧妙。」芝加哥大學的心理學者尼可拉斯.艾普利(Nicholas Epley)對科學雜誌《鸚鵡螺》(Nautilus)說,那年是二○一五。「同樣的狀況也適用在你身上。知己莫若己,你若是一門科目,那你就是此間的專家——你曾看著自己一路走來,你不知道自己晚上去參加派對是何等光鮮亮麗,你也知道自己那天早上醒來時如何地唉聲嘆氣;你對自己的資訊掌握非常豐碩⋯⋯所以你可以如專家似地對自己評說。」
顧及在《創業鯊魚幫》節目上凍僵的史蒂芬.阿爾斯托,我希望這裡的教訓會是他砸的鍋沒有人會注意到,但YouTube上二十五萬次的點擊與觀看,就擺在那裡,我實在沒有辦法睜眼說瞎話。別人是會注意到你的,尤其是聚光燈下的你。回顧二○一三年的奧斯卡金像獎盛事,珍妮佛.勞倫斯(Jennifer Lawrence)在去領最佳女主角獎的階梯上絆倒,叫人想看不到都無法。再回想第五章,我說過自己在職涯初期開過些尷尬會議。我知道自己當時內心的漣漪,在別人眼裡不見得非常清晰。但話說回來,也有些時候我知道自己在旁人眼裡非常透明。
曾經有一回,我的整個上半身都充血發紅——不是只有臉紅而已,而是連我的脖子跟手臂都起了反應。我工作上最好的朋友,卡麗莎,那天坐在我的旁邊,而在我演講完畢後,她手伸了過來,把食指按壓在了我的前臂上,就像你在測試曬傷有多嚴重一樣。就這樣,我們倆一起看著我手臂上的皮膚因為被壓而顏色變淡了一下下,然後卡麗莎一放手又變紅回去。但對於十足閉俗的人,這兒有另外一個好消息是:就算別人真的注意到你砸鍋好了,他們的態度也不見得如你所想的那般幸災樂禍。
稍晚——同樣由吉洛維奇執筆的——一篇論文裡詳述的一系列後續研究,將這一點應用到了日常尷尬的另外一個區塊:早起頭髮亂翹的日子。在一整個學期的時間跨度中,一名實驗者會隨機挑選五天闖進康乃爾大學的某心理學講座課程,然後在現場發放研究問卷給同學們,讓他們給其他同學的外表打分數:比起平時上學日的模樣,今天的同學帥不帥,美不美。此外,他們也要同樣以平日水準當作標竿,對當日的自己品頭論足——而且是要嘗試以其他同學的視角來這麼做。
在這個實驗裡,吉洛維奇與論文共同作者又再一次發現了「聚光燈效應」存在的證據:受測學生看到自身的缺陷,然後預期同學對他們的評價會隨之波動。但他們自己對同學的評價卻是連五回都相當穩定,沒有什麼大的變化。「我們自認非常刺眼而耿耿於懷的臉斑或翹髮,其實一般人根本不會拿放大鏡去看。」吉洛維奇跟同僚如此寫道。多數人自己的斑跟翹髮都看不完了,哪有時間看別人的斑跟翹髮。
會起心動念要研究聚光燈效應,是因為吉洛維奇曾研究過「後悔」,這是他在聊天時告訴我的。有句話常被po在IG或Pinteres上頭,不知各位有沒有看過?「二十年後你會失望的,不是你現在做了什麼,而是你現在沒做什麼。」那句話是這麼說的。很多人常以訛傳訛地把這句話塞進馬克.吐溫的嘴裡,但它真正的出處其實是一九九一年由小H.傑克森.布朗(H. Jackson Brown Jr.)寫成的回憶錄《P.S. 我愛你:媽寫的東西,都是好酒沉甕底 》(P.S. I Love You: When Mom Wrote, She Always Saved the Best for Last)。布朗的母親說這句話,其實是感性地在鼓勵自己的兒子,但理性去分析其字面上的意思,布朗媽的發言其實也經得起檢驗。
確實根據由吉洛維奇等人所進行的研究,人真的是縮起來比做下去更容易後悔。我們會決定不採取行動,通常都是因為害怕導致社交上或人際間的尷尬:要是你答應上台演講,要是你搶先告白說「我愛你」,別人會怎麼說?會怎麼想?「若那真的是你的煩惱——你知道的,你在別人眼裡會是什麼模樣?——那你得納入腦考量的一點——做好心理準備好了嗎?——從一開始,就沒有那麼多人會注意你是什麼模樣。」吉洛維奇這麼告訴我。所以讓你糾結的事情即便尷尬,還是去做做看吧,即便是為了讓自己將來沒有遺憾都好。
書籍介紹
本文摘錄自《尷尬學:尷尬的瞬間,是我們考驗自己的機會》,河景書房出版
*透過以上連結購書,《關鍵評論網》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。
作者:梅莉莎・達爾(Melissa Dahl)
譯者:鄭煥昇
在會議中暢所欲言後你感覺非常棒,但現場每個人卻一語不發……
鄰居說完「哈囉」,而你竟回答「謝謝,我很好」……
突然發現廚房的菜瓜布黏在毛衣上,而你已經走過兩條大馬路……
這些瞬間都會讓人冷汗直流,但你有沒有想過或許這些至為尷尬的時刻,
其實是我們的人生至寶?
梅莉莎・達爾身為《New York》雜誌旗下「Science of Us」網站的共同創辦人,對尷尬的處境一點也不陌生。
在尷尬了一輩子之後,她的好奇心盯上了「尷尬」:這種人皆有之但沒人多瞧過兩眼的情緒。於是她踏上了對尷尬一探究竟的旅程──結果她發現,尷尬其實可以充實我們的人生:尷尬不必然會讓我們感覺孤單,事實上,但凡所有會讓我們尷尬的人事物,都在提醒著我們彼此間的羈絆。
在本書裡,達爾親炙了人世間最怪誕、最令人視為畏途的尷尬角落。
她鼓起勇氣與陌生人在匆促繁忙的紐約地鐵裡聊天,她咬著手帕用純友誼版Tinder約了網友見面,她拚了老命報名成為即興喜劇課程的學生,她甚至豁出去,把中學日記唸給一群素昧平生的觀眾聆聽!
在體驗這一切後,她懂得了一個道理:尷尬的瞬間,是我們考驗自己的機會。當其他人都在裝酷、裝冷豔的時候,你可以比他們更勇敢,更寬容──也在同時間更不畏尷尬地做自己一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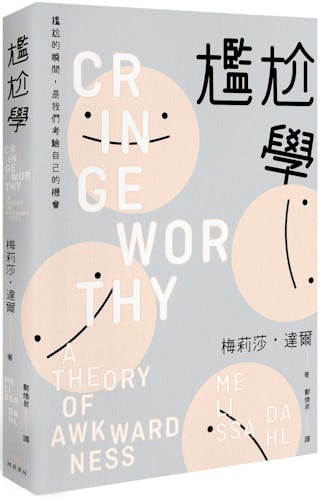
責任編輯:翁世航
核稿編輯:丁肇九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