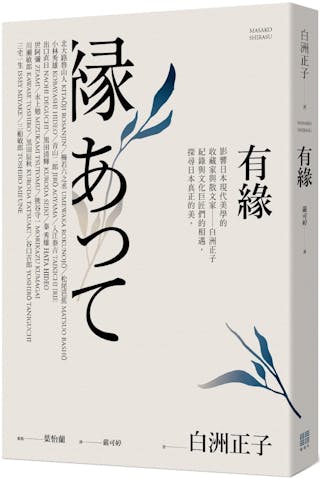文:白洲正子
瀧的聯想
瀧,光聽到這個詞,內心就感到無比雀躍。不僅因為有瀑布的風景分外優美,也因為自古以來,落個不停的轟轟水聲與大自然形成的造化,同樣打動人心。而且三點水加上龍的字體令我深感魅力。從湍急落下的水勢看出龍騰的姿勢,需要多麼豐富的想像力。與其說是魅力,或許更該說那是象形文字本身的魔力。
不過,瀧本來應該寫作「瀑布」,據說三點水加上龍有浸濕、潤澤的意思,所以象徵著急流。的確瀑布給人的印象更為壯觀,用來稱呼「尼加拉瀑布」或「優勝美地瀑布」或許更為合適。不過像日本的瀧,即使是規模較大的「那智之瀧」,仍與瀑布的名稱不符。這跟周圍的環境或許也有關,我去欣賞美國的瀑布時,雖然對於當地大陸式的壯觀景象感到驚奇,卻沒什麼特別的感觸。倒不是我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,這其中是有歷史的。日本也不是完全沒在用「瀑布」這個詞,只是我們無意識地仍會唸成「瀧」。瀧彷彿近在我們身邊,如同水流一般,是自從太古以來流傳至今,令人懷舊的詞彙。
當漢字剛傳到日本時,我們的祖先為「瀧」的發音「taki」配上多岐、多藝、多紀等漢字。其中多半是指河川的急流,由此可見,前人對「瀧」這個字的理解是正確的。
每年都想看見,吉野一帶的河川湧現洶湧的白波。
在高聳的山勢下,滾滾瀑布渦流如白木綿花般鮮明,百看不厭。
這是元正天皇巡幸吉野離宮時,在笠金村所作的兩首和歌。除此之外,在其他的場合,瀧幾乎都指河川的急流。在《萬葉集》時代的人們未必不知道深山幽谷的瀑布,但他們專門歌詠日常生活中的事物。元明天皇前往「養老之瀧」舉行祓禊儀式時,大伴東人與家持作出以下的和歌:
這條瀧形成的流水,就是傳說中的返老還童之泉。
或許是因為田跡川之瀧很清澈,自古以來在這片多藝野之地,就立有行宮。
在和歌的前言提及「記於美濃國多藝行宮」,養老之瀧與吉野川不同,雖然規模較大,堪稱為瀑布,但是依然叫作「瀧」,仍是「瀧之淺溪」。古代的人們或許不拘小節,不太區分這些細節,不過我總覺得古人並不喜歡「瀑布」這樣的字眼。如果說「不喜歡」並不恰當,或許他們從這個詞感受到一種屬於大陸的氣勢,那是大和語彙所無法涵蓋的。於是在不知不覺間,無論瀑布或急流同樣都稱為「瀧」,兩者開始混同。即使是稱不上瀧的落水口,人們也面不改色地稱為「瀧之御門」。
即使在東邊的瀧之御門守候,不論昨天或今天,都聽不到皇子的召喚。
這首和歌是哀悼草壁皇子的薨逝,由舍人所作的輓歌之一,從勾池通到宮殿的水溝,附近的水門稱為「瀧之御門」。後來清涼殿東北方的溝稱為「瀧口」,或許兩者之間多少有些關聯。而在這裡守護的侍衛,也因而有「瀧口」的別稱。
現在有「重返青春之水」的詞出現,清澈的水可讓老人變年輕的「復活」思想,從神代以來就存在於日本。有所謂「變若水」的信仰,祓禊就是其中一種。這種信仰認為藉著用水清潔身體,可以讓靈魂復甦。其中又以從深山流出的清冽瀧水最有效,因此瀧本身也成為一種信仰。「那智之瀧」至今仍是神靈的象徵,前方立有鳥居。還有很多其他類似的場所,幾乎為人所熟知的瀧,好像都已經神格化了。
對於瀑布的崇拜不僅限於日本。印地安人也將尼加拉瀑布、優勝美地瀑布視為神靈崇拜。非洲土著為了平息神明的怒氣,會向據說是世界最大的「卡蘭博瀑布」以活人獻祭。說到犧牲,在《熊野曼荼羅》等宗教繪畫中,瀧的旁邊畫著白馬,我一直覺得不可思議;請教過永瀨嘉平先生,原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,日本仍存在著砍馬或牛的頭,投入瀧底水潭的習俗。主要是作為祈雨的儀式,據說是藉由污染清水激怒龍神,迫使龍神登上天降雨,這是帶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民間信仰。或許在最初並沒有砍下動物的頭,而是向龍神獻上美麗的白馬吧。在池水中有著馬形的岩石,瀨戶的工匠也以土製成馬的形狀,向神明供奉,神社的神馬也一定是白馬,這都是源自同樣的想法。
話題稍微有點偏離,同樣出自民間信仰,但是有別於非洲的土著,日本人對於瀧的迷信已提升到一種思想的境界,或者也可以說,發展為儀式的形態。從古代的重返年輕之水與祓禊的風俗,都可以看出這種思想的萌芽。隨著佛教盛行,待在瀧底下承受水擊滌淨,成為一種重要的修行。這正是太古神明的「復活」,透過佛教,瀧甚至獲得新生。我們也可以說,以瀧為媒介,神祇信仰與佛教混淆在一起,至少接受落水沖擊,可說是神佛混淆最明顯的例子。
在文德天皇時代(九世紀中期),有位名叫相應和尚的山岳修行者,住在比叡山。他自幼信仰虔誠,在十九歲時發願敬拜不動明王的真身,耗費三年的時間在比叡、比良山之間徘徊。據說比良山分佈著十九處瀧,他在這些瀧底下接受沖擊,一心專注於修行,但是不動明王始終不現真身。他感到疲乏困頓,走到比良山深處的葛川時,由當地人帶到「三之瀧」。他在那裡經過七天斷食,虔心祈願,於是看到在水氣瀰漫中,不動明王從瀧下的水潭中出現。相應和尚大喜過望,跳下水潭抱住不動明王,等他清醒過來時,發現自己抱著一株老桂樹。因此他用這棵桂樹的木材雕刻剛剛看到的不動明王尊像,建立寺廟祭祀,據說就是現在的「葛川明王院」。
這段故事我曾在《比叡山回峰行》一書中詳細提及,在這裡簡單記下,因為在關於瀧的傳說中,這個故事最為動人。而更令人訝異的是,現在仍有許多回峰行者遵循相應和尚立下的傳統,在山中巡行後來到葛川,接受「三之瀧」的沖擊,對於瀧的信仰在現實中依然存在,令我覺得感動。像是在清水寺的「音羽之瀧」、愛宕山的「空也之瀧」以及其他聖地,我都曾見過有人在瀧下修行,但是將瀧之信仰提升到藝術境界的,也只有比叡山的「回峰行」。山之靜與水之動,這樣的哲學不僅存在於我國的宗教,也滲透至一般文化中,我想這麼說並不為過吧。
提起瀧,我總會想起根津美術館收藏的《那智之瀧圖》,畫作令人感受到神聖而靜謐,而且水勢相當強勁。這是前述《熊野曼荼羅》的原型,而且這不僅是繪畫,畫中的瀧也象徵著人們的信仰。眾所周知,那智山是熊野三山之一,正如前面所提到的,人們將那智之瀧視為神的化身。前年我去那裡的時候——雖然已經三月底,雪下得很大。風雪包覆著高大的杉木,上方的山與天空彷彿融為一體,什麼都看不見。在整片白茫芒的景象中,激流崩落而下的瀧予人相當強烈的印象,的確只能以「神」這個字形容。我不喜歡說得太誇張,但是在人的一生中,確實難有幾次機會體驗這樣的情景。當時我切身感受到《那智之瀧圖》與日本的「瀧」字所象徵的意義。
 那智之瀧/Photo Credit: Shutterstock / 達志影像
那智之瀧/Photo Credit: Shutterstock / 達志影像 不過,瀧並不只是近在眼前看時才美。當我第一次去那智之瀧時,從阿彌陀峰隔著一座山遠眺熊野灘,忽然聽到從遠處傳來彷彿是飛機的轟隆聲。但是無論我朝天空看,或是往下眺望,都看不到任何像飛機的物體。當我無意間將視線移向左邊的山,看到在深綠色的森林間,劃出一條白色的細線。在那一瞬間,我感受到彷彿整座山都在發出轟鳴。那是我首次親眼目睹「那智之瀧」,還記得出於無以名狀的感動,我甚至渾身顫抖。
座落於宇治鷲峰山的金胎寺,是山伏的必經之地,寺頂上照例立著行者的石像,朝著吉野大峰的方向。那裡已是險峻的岩地,瀧水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。既然已經來到這裡,我想親眼看看附近的瀧,於是我沿途邊握著樹枝往下移動,但是往右移動就聽到瀑布在左邊,繞到左邊就聽到瀑布在右邊。不知不覺已近黃昏,只好放棄回來。當時的水聲始終沒有消失,即使我寫到這裡,仍迴響在耳際。即使是只聽得到水聲,卻看不到的瀧,其實也別有意趣。
日本的瀧從史前即成為一種信仰,曾有無數和歌吟詠過,描繪在畫中,尤其成為山水畫中不可或缺的點綴。譬如收藏於河內金剛寺的《日月山水屏風》,別忘了在貌似葛城山的雪景中,還畫著小小的一條瀧。這種構圖也出現在中國的南畫中,藉由描繪深山幽谷中的瀑布,表現心中的理想境界,可說是勾勒出另一個不同的世界。即使小也無妨,瀧是山不可或缺的象徵,水是神的住所。不論是花、紅葉、人們的生活,都受到流水的滋潤,所以水是生靈與生命的根源。不論是春季的山或雪景,在變幻無常轉瞬即逝的世界上,只有瀧是恆久不變的生命泉源。同樣的象徵可說也出現在《熊野曼荼羅》,瀧的存在區分了人間及死後的世界,由此可知背景是那智山的「奧之院」(瀧見寺)。《日月山水屏風》與《熊野曼荼羅》都是室町時代的作品,對照鎌倉時代的《那智的瀧圖》,可感受到關於「瀧」的概念變得更為豐富,甚至帶有密宗的色彩。不變的是,瀧依然與人類的生命有著密切相聯,與中國畫的瀑布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。
在《古事記》中,瀧以女神的樣貌出現。天照大神與須佐男之命在天之安河賭誓時,首先誕生的是「多紀理毘賣命」。美麗而富有野性的瀧之神竟然是女神,這點很有意思。通常跟水有關係的神都是女神,不過我認為《古事記》不只是神話,更適切地捕捉了自然的樣貌(其中也包括人)。瀧這個字或許就是出自多紀理毘賣命,象徵著所有能量的源頭。現在瀧仍是水力的來源,而撼動天地的水聲,以及導致岩石崩裂的水勢,就像容易爆怒降災的神靈,令人畏懼。另一方面,瀧也是美麗的。春天帶有櫻花的香氣,秋日點綴著紅葉,不僅具備了各種女性化的條件,隨著觀點不同甚至帶有情色的意味。對於豐穰女神而言,情色是必然的屬性,但碎裂岩石落下的水流,更像是女性的身軀。或許出於這個原因,現在各地仍有落水稱為「產之瀧」(或「三之瀧」),人們會透過瀧祈求平安順產。據說葛川的「三之瀧」,正是由於不動明王而湧現。
「瀑布」正如字面的意象,是形容像白布垂掛的樣子。人們的想法差異不大,外國有瀑布稱為「新娘的面紗」,聽說日本北海道也有瀧稱為「新娘的禮服」。這當然是最近新取的名字,像「白系之瀧」、「布引之瀧」、「白絹之瀧」等,都與垂吊著布的情景類似,反而是「瀑布」繼承了瀧這個名字的感覺。不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:不動、權現、華嚴、般若、彌勒、阿彌陀、觀音等與佛教有關的名稱,其中又以「不動之瀧」壓倒性地佔多數。這是因為修驗道的行者信奉不動明王,相信接受落水沖擊將有所感悟,甚至自己也將得道。「變若水」的信仰也以這種形態延續下來。「阿彌陀之瀧」與「觀音之瀧」,或許也各別傳承了某一部分,而青森縣三戶郡田子町的「彌勒之瀧」,背後則有悲傷的故事。
在日本的南北朝時代,有位周遊諸國的行腳僧曾在瀧下修行,但受到當地人排斥,因此餓死,或許人們認為他褻瀆了神聖的水神。由於亡靈作祟,村裡的災難不絕。有一天某位雲遊僧人行經此地,將自己信仰的彌勒之名送給瀧,才得以平息怨靈,使當地恢復平靜。
也有些瀧是依據周遭的景色與狀況命名。
譬如「雙門之瀧」是由兩條瀧流入同一水潭,「暗門之瀧」是指瀧落在沒有日光照射的谷間。「吹割之瀧」是由瀧穿透岩石並有水霧瀰漫,「光之瀧」正如其名,在日光照射下閃耀美麗的光彩。除了「雷瀧」、「霹靂瀧」、「轟瀧」、「咆嘯之瀧」、「樹靈之瀧」、「轆轤之瀧」、「鼓之瀧」、「琴瀧」、「琵琶瀧」等帶有水聲的名字,還有「白瀧」、「白水之瀧」、「赤瀧」、「緋瀧」、「五色之瀧」、「藍瓶之瀧」等反映岩壁顏色的名稱。特別令人感到哀傷的,是以投水自盡者命名,譬如「阿冒念之瀧」、「君之瀧」、「佛御前之瀧」等,不勝枚舉。
書籍介紹
本文摘錄自《有緣》,榻榻米出版
*透過以上連結購書,《關鍵評論網》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。
作者:白洲正子
譯者:嚴可婷
兩屆「讀賣文學獎」得主,影響日本現代美學的收藏家與散文家──白洲正子,
紀錄與文化巨匠們的每一次相遇,探尋日本真正的美。
在戰爭使日本喪失一切的時代,我無法保持內心的平靜,總想遇見一些「人」,莫名地渴望接觸「美的事物」,為此四處奔波。也因為如此,我接觸到許多美的事物,獲得許多良師益友。……如今回想起來,這些人所教導我的是:活在有限的當下、享受生命。「此時此刻」逝而不返,再也不可能重現。想到這一點,就知道必須要珍惜光陰,把握每次偶然的相逢,幸福地渡過僅此一次的人生。──白洲正子
二次戰後,日本傳統文化在經濟飛速的進展下如飄零的櫻花漸漸散落,白洲正子因此踏上追尋昔日舊物之美的旅程,與多位日本文化巨匠對「美的事物」有深刻的對話與交流:北大路魯山人、梅若六之丞、黑田清輝、川瀨敏郎、谷口吉郎、水上勉……,漫談能樂、和歌、陶器、茶道、花道、民藝、繪畫、攝影……在巨匠們的作品中探尋日本真正的美,白洲正子那簡單而質樸的美學觀,至今影響著日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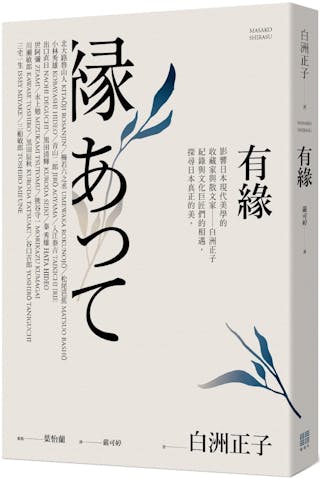
責任編輯:潘柏翰
核稿編輯:翁世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