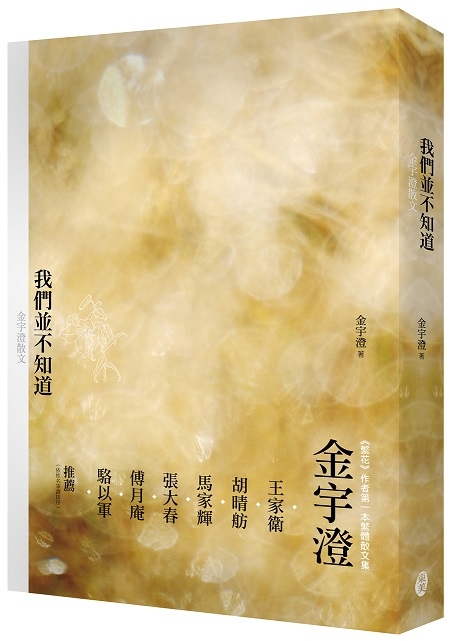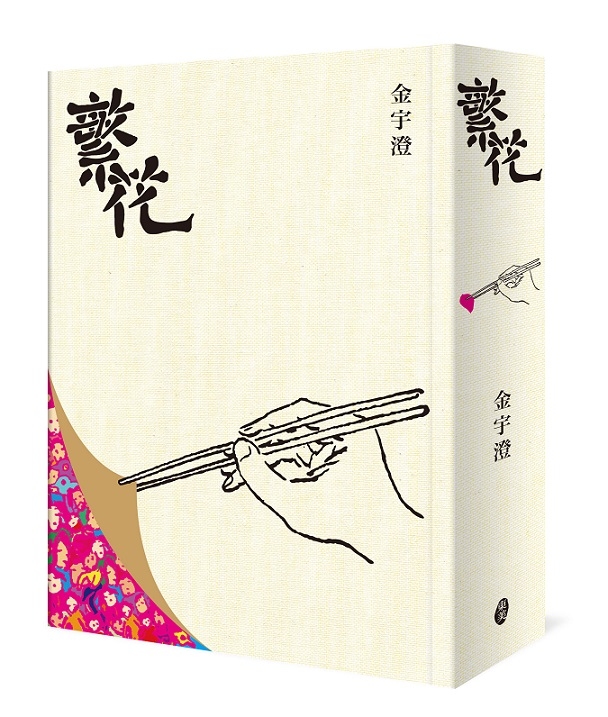文|李桐豪 日期|2017.03.1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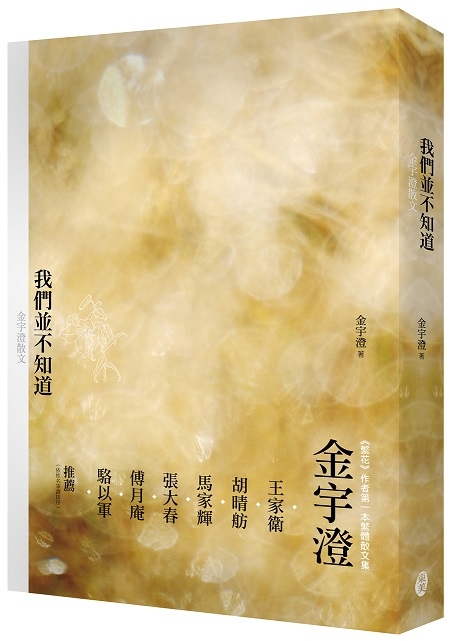
我們並不知道:金宇澄散文
《我們並不知道》裡有個故事是這樣說的:上海小青年文革下鄉黑龍江,於農場與一中年勞改犯學做鐮刀柄。論資歷,中年勞改犯是小青年前輩,但老前輩講南方官話,斯文有禮,為人客氣。上海小青年自家鄉帶來了唱機,工具間終日播放,聽貝多芬和蕭邦,樂聲引來知音,被流放天涯的淪落人在冬夜裡組樂團作文藝排練,老前輩在一旁加煤燒水也不言語。一夜,樂團排練進入高潮,燒火的老前輩挺直腰桿說「交關好」、「霞氣好」,那是上海話「非常」之意,老前輩口音洩漏了來歷,小青年詢問之下,始知老前輩是舊上海樂隊的小提琴手。最沉默的,才是最深情的知音。
這個能人異士大隱於市的故事極其類似金宇澄本人際遇,他在80年代寫了幾部小說,得獎了,並未趁勝追擊,反而轉進文學雜誌社當編輯,寂寞了一輩子,只為人作嫁。四年前,老先生在網路以「獨上閣樓」的名號追憶上海似水年華,他沒別的心思,就只是分享,誰知就有網友在旁敲碗求帖,應觀眾要求,一回寫過一回,再回神,就是厚得如小磚頭一樣的小說《繁花》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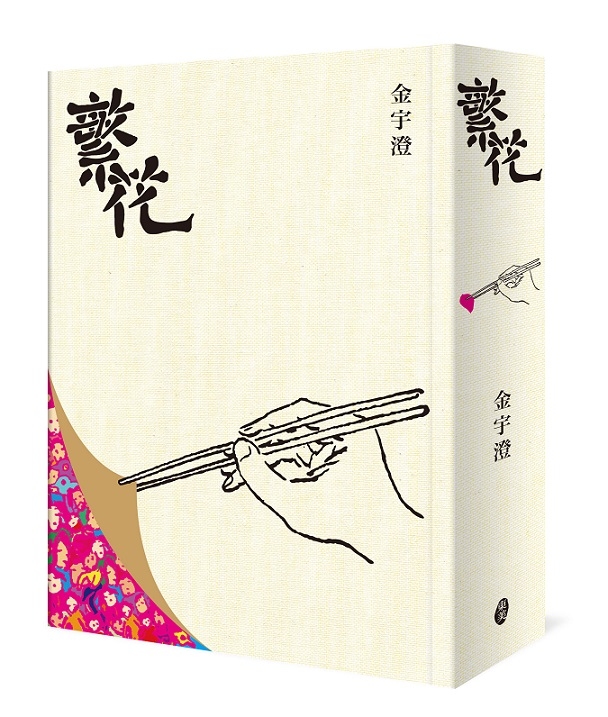
繁花
《繁花》計35萬字,有個單字出現了1500次,「不響」,一聲不響的不響,這是好事者算過了:女人邀請男人喝咖啡,男人不響。飯桌上,男人被戳中了心事,不響。男人喝醉了,閉上眼睛,不響。傷心不響,沉思不響,發呆不響。扉頁還是一句「上帝不響,像一切由我決定」。
不響,是心裡有事,是詞窮,是故作神祕,評論家有千百種文學修辭的理由,但也可能不響的理由就只有一種,迷人的男人從來不廢話,博學而健談是一回事,但健談卻不懂節制,太得意了,梁朝偉也把自己聊成了曾志偉。男人談話是這樣,寫作也是,最迷人的寫作往往都是博學而節制,阿城是這樣,木心是這樣,金宇澄也是這樣。算算年紀,老先生今年64歲,王安憶63,蘇童54,畢飛宇53,老先生出名不趁早,因為多少往事鎖在心裡,一生不響,故「文學潛伏者」臨老入花叢,方得一鳴驚人。
沉默是金的魅力在《我們並不知道》看得更清楚,該書原名《洗牌年代》,出版早於《繁花》,小毛蓓蒂的故事老先生說了兩遍,兩相對照互為前世今生,只是少了長篇小說的布局。《我們並不知道》裡上海浮花浪蕊的往事,點到為止,更簡白,沒看過《繁花》無妨,亦可把它當作一本上海往事錄。他寫上海的男人,上海的女人,上海人的小奸小壞,「拍拍頭頂、腳底板也會響的上海人」,也可以當張愛玲的散文《流言》來看待。
金宇澄1952年生,出生那年,張愛玲離開上海,「50年代父母取名隨便,哥哥第一個生,比較忙亂,就叫金芒芒,我是第二個,舒服一點,就叫金舒舒,上海話拗口,很不好聽,有資產階級味道,」他在對岸的訪問說道:「文革時爸爸幫我改掉,取自毛澤東詩詞金猴奮起千鈞棒,玉宇澄清萬里埃,現在金宇澄這個陌生名字,有個80後的讀者說,大概是韓國人吧。」他出生知識分子家庭,卻在庶民生活裡長大,文革期間與哥哥下鄉黑龍江,年復一年種玉米大豆,做泥瓦匠,蓋房、砌牆、做石工,伐木,出窯。
老先生寫文革,不提傷痕,不憶苦思甜,一樣不響(受過「迫害」更容易走紅不是?)。他只講文革的日常,掏井,打油,補缸,磨豆腐,也幫發情的小馬做閹割,他在書末與傅月庵的對談裡解釋少年時代多能鄙事,是「人在平靜無望階段,容易被所謂的技能滲透。做馬夫,不知道要做到哪一年,就會接受細節了」種種勞動充滿細節,但行文有節制,讀來全然不瑣碎,譬如《天工開物》一樣樸素。
老先生講技藝,也講記憶,北大荒的淒涼對照著老上海的繁華,淒涼處憶繁華,繁華處有淒涼,但也許也沒這樣濫情,回憶是不值錢的,是「西洋老地磚讓幾代人繡花拖鞋、皮拖鞋、夾腳拖鞋、廣式木拖板、鬆緊鞋磨去了洛可可紋樣,留下雲霓狀一片死灰」,但動盪的年代,紅五類、黑五類,知青、解放軍、兵工農所,眾人身世階級,南北串聯,全像一副撲克牌一樣刷刷刷打散重來的年代,身不由己,也只能靠一點點死灰的回憶做支撐,記住自己的出處。老先生文集以《洗牌年代》之,或許是這樣一點念想。而我們並不知道,小資產階級捧著一本《繁花》,懷念著不存在的老上海,也大抵如此。
李桐豪
就是Dirty Talk,老牌新聞台「對我說髒話」台長。Flower、Friend、Fortune、Family,只要F開頭的字眼都喜歡。紅十字會救生教練,出過兩本書《絲路分手旅行》和《綁架張愛玲》。
OKAPI專欄「女作家愛情必勝兵法」「瘋狂辦公室」作者,偶爾也寫「作家讀書筆記」。

《繁花(全新修訂布面精裝典藏版)》
作者:金宇澄
出版社: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:2019/10/31
語言:繁體中文
定價:630元
ISBN:9789869820141
規格:精裝 / 624頁 / 15 x 21 x 3.12 cm / 普通級 / 單色印刷 / 初版
出版地:台灣
購買往此去→https://www.donmay.com.tw/products/9789869820141

《我們並不知道:金宇澄散文》
作者: 金宇澄
出版社: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:2017/01/20
語言:繁體中文
定價:380元
ISBN:9789869213912
規格:平裝 / 328頁 /15 x 21 cm / 普通級 / 全彩印刷 / 初版
出版地:台灣
購買往此去→https://www.donmay.com.tw/products/9789869213912